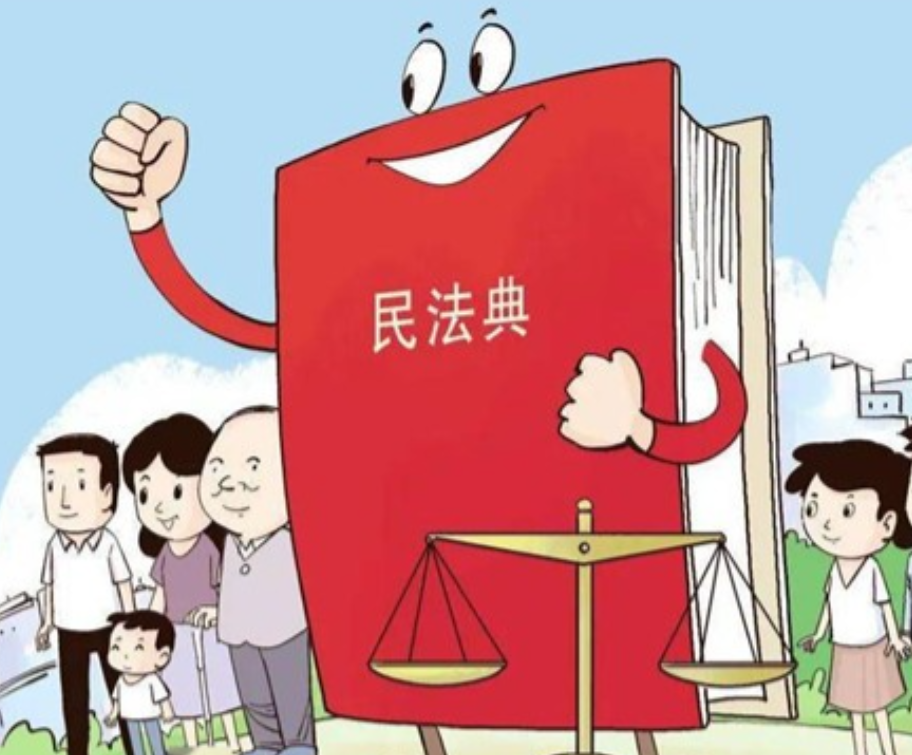湖南,某山村突发揪心一幕!52岁热心村民连续3天义务帮邻家操办丧事,抬棺至陡坡时突发心梗猝死,棺木坠地震翻引骚动!遗孀哭诉“累死的”索赔9万遭拒,主家咬定“自愿帮忙”。一审中,一纸鉴定揭真相:抬棺负重150公斤成“催命符”,连续高强度劳动直接诱发基础病!经过审理,法院这样判决。一场丧事毁了两个家庭,法律撕开乡村“人情债”潜规则——无偿帮忙≠无责!好心为何变成“致命代价”?这场情与法的较量,您站哪边?
(案件来源:裁判文书网)
暮色中的湘西村落,一声悲怆的哭喊划破天际。52岁的陈永福(化名)循声奔至邻家,只见83岁的王德发(化名)老人安卧床榻,子女王建军、王建民正伏地痛哭。
这个被村民称作"永福叔"的热心汉子,当即挽起衣袖操持起丧事——连夜采买孝布、搭建灵堂、协调出殡事宜,全然忘却自己数日前刚因胸闷就医。
三日后送葬队伍行至村口陡坡,陈永福作为头杠抬棺人突感胸痛如绞。
同杠的吴大勇(化名)察觉异样时,陈永福已面色青紫瘫倒在地。
剧烈震颤中,棺木轰然坠地,纸钱纷飞间,这位义务操持三日的帮工再未醒来。
法医鉴定显示:急性心肌梗死致心源性猝死。
遗孀周淑珍(化名)索赔9万,但遭到拒绝。无奈之下,周淑珍诉至法院。
王建军坚称:"永福叔自愿帮忙,我们没请也没付钱!"周淑珍泣诉:"他帮着操劳三天,累得发病走了啊!"
那么,法院会如何判决呢?
首先,本案中,陈永福与王德发家的义务帮工关系是否成立?
在无偿帮工法律关系中,核心在于判断“被帮工人的接受行为”是否成立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五条强调“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”的默示同意规则。
本案中,陈永福连续三日参与丧事筹备,从采买孝布到抬棺的全过程,主家王建军兄弟未有任何劝阻行为,反而允许其承担核心劳务(如头杠抬棺),实质上构成对帮工行为的持续性接受。
一方面,陈永福的帮工行为贯穿丧事全程,非临时性、偶发性协助,符合持续性行为参与。
另一方面,王德发家实际受益,丧事作为农村重大仪式,主家依赖帮工完成抬棺等核心环节。
同时,主家作为丧事组织者,完全具备筛选帮工人员、告知风险的能力。
本案法院通过行为外观与实质受益的双重标准,确认帮工关系成立,体现了法律对弱势帮工群体的倾向性保护。
其次,帮工活动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?
一方面,从医学角度,司法鉴定显示,陈永福抬棺时人均负重达150公斤,且连续三日高强度劳动导致肾上腺素激增、血压升高,直接触发冠状动脉斑块破裂,符合急性心梗的病理机制。其死亡并非单纯自身疾病发展结果,而是外因(体力负荷)与内因(高血压病史)共同作用所致。
另一方面,在法律层面,若帮工活动显著提升损害发生概率,即使损害由自身疾病引发,仍应认定因果关系。
本案中,抬棺属于明确的高强度劳动,主家未对参与者进行基础健康问询,放任高血压患者从事高危作业,使得本可避免的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。
司法实践中,自身疾病通常仅影响责任比例,而非否定因果关系。若帮工活动是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,即便疾病为主要原因,被帮工人仍须担责。
法院采用“条件关系+相当性”双重标准,认定帮工活动与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
最后,本案责任承担比例如何划分?
本案中,农村丧事中抬棺属公认重体力劳动,主家应当预见高血压患者参与的风险,但是,主家未进行基本健康筛查、未提供辅助工具(如滑轮减负)、未安排人员替换轮休。在陈永福发病时,现场无急救设备或专业人员,延误救治时机。
也就是说,主家存在过错,应当承担一定责任。
不过,陈永福未主动告知近期胸闷就诊记录,违反如实告知义务,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明知自身健康状态仍选择参与高危活动,应当承担主要责任。同时,陈永福发病初期未及时退出劳动,导致损害扩大。
基于此,法院判定主家承担40%责任、死者自负60%。
对于本案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