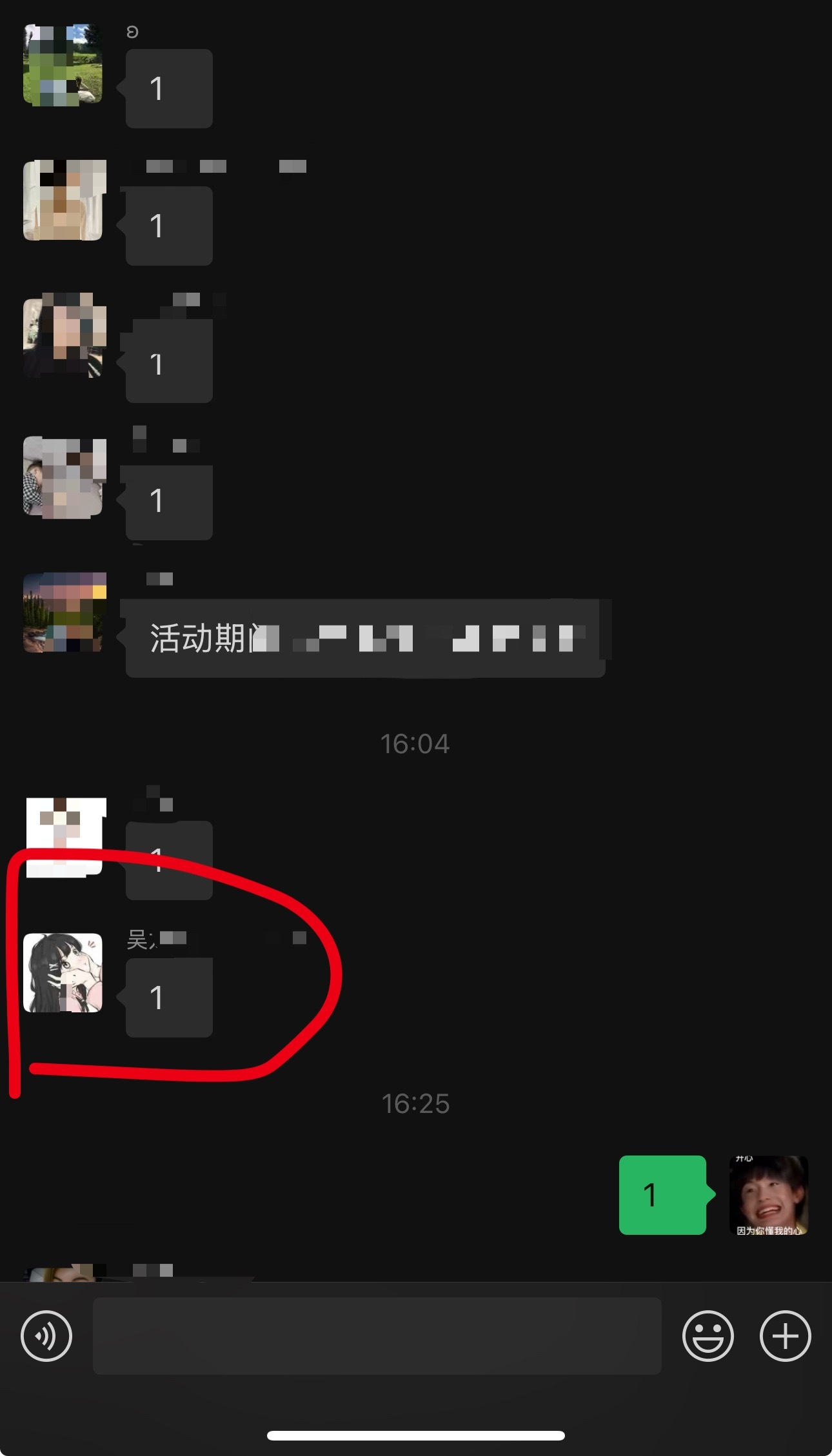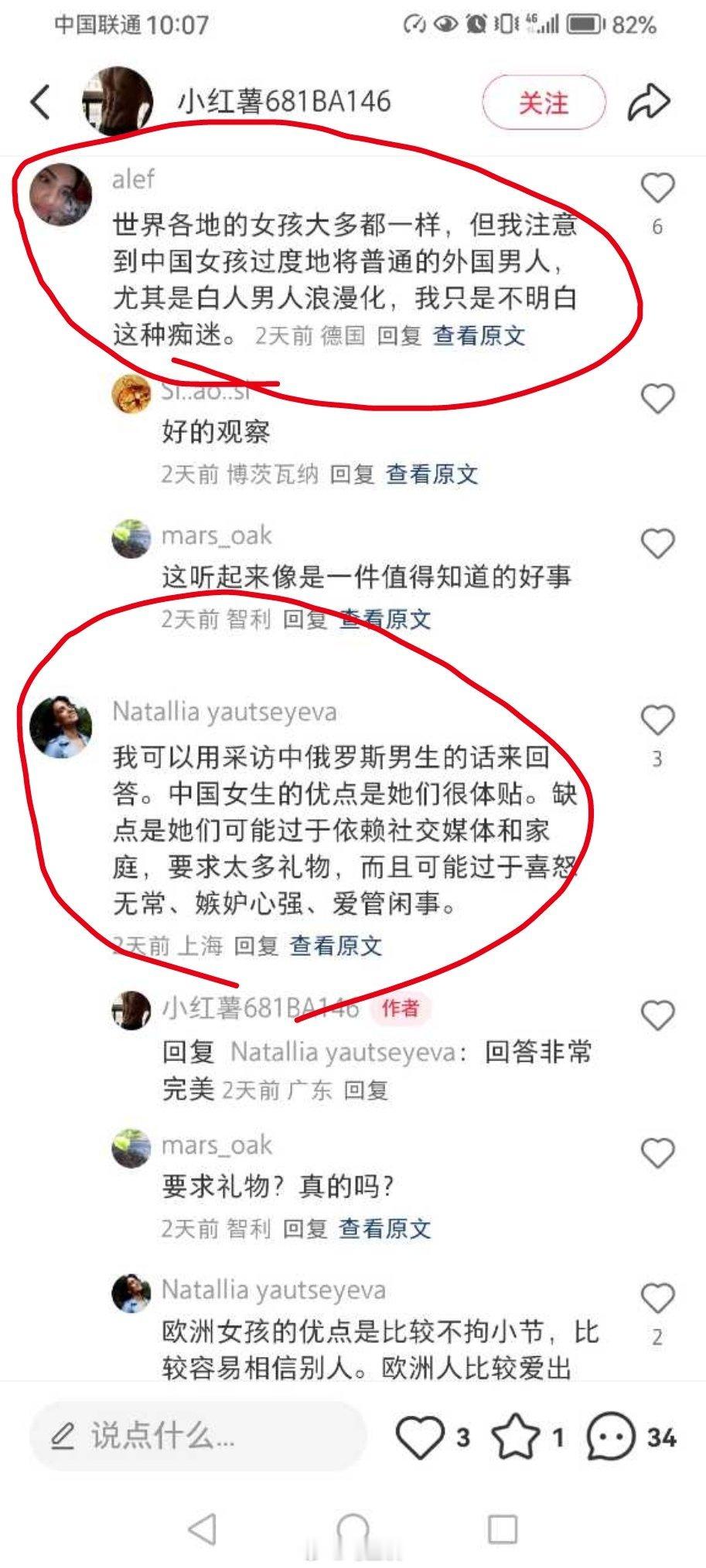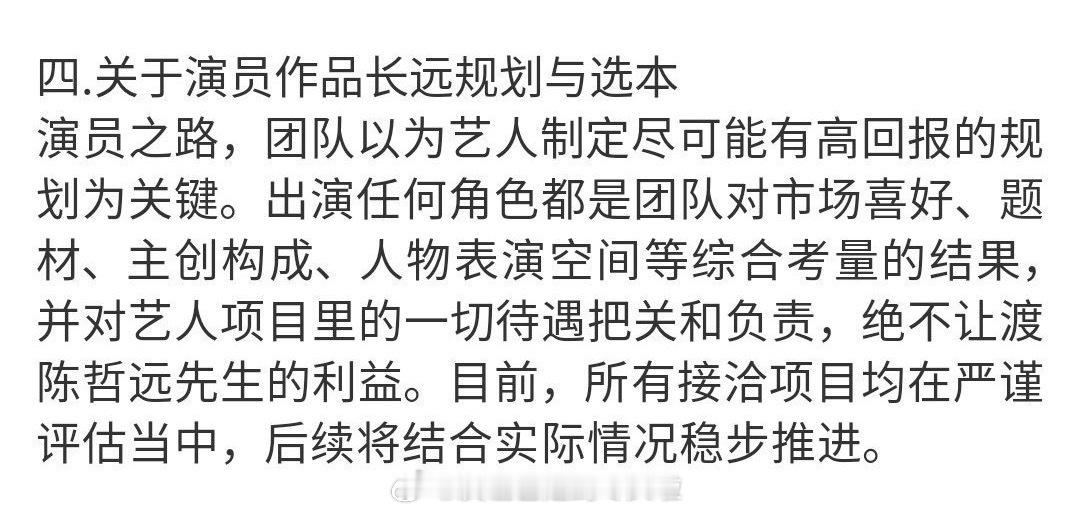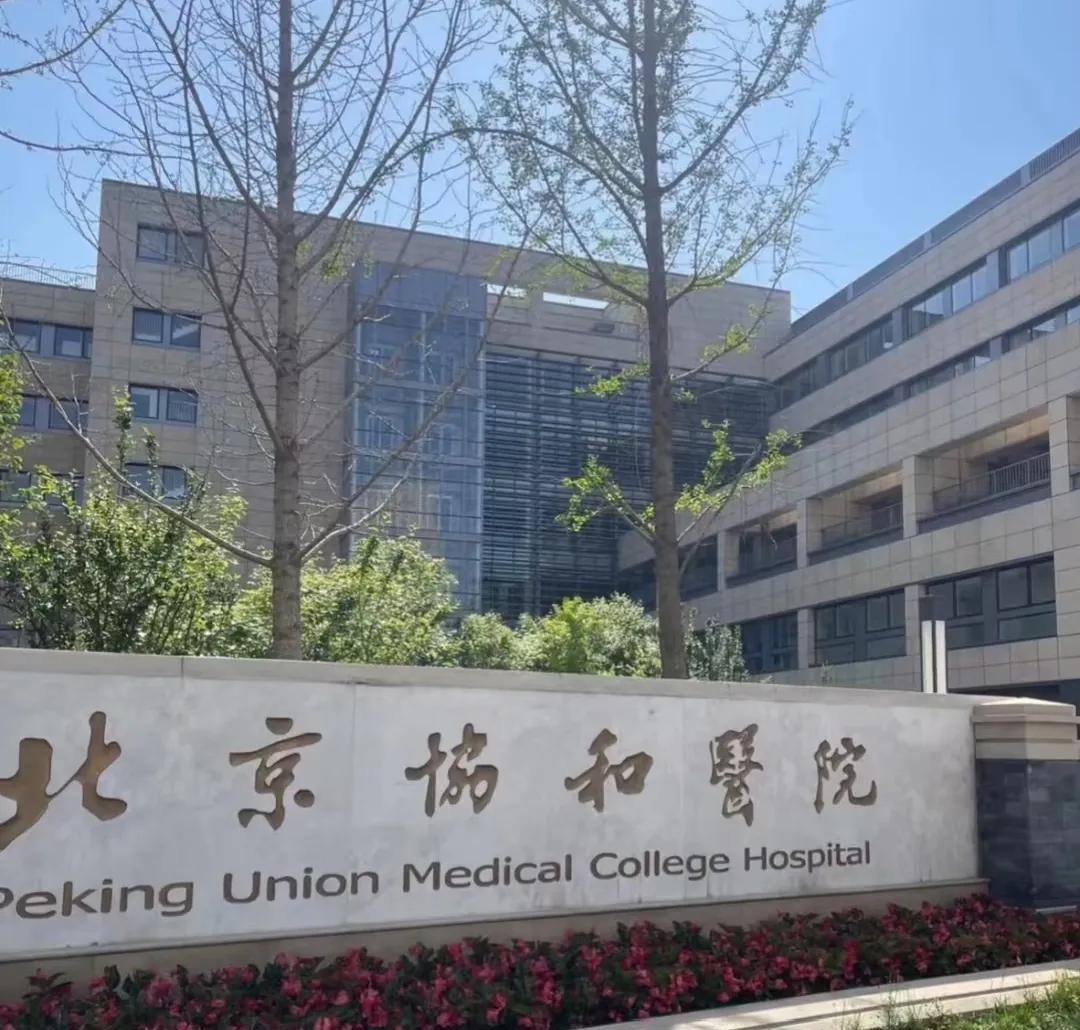9年前,河南一位93岁的拾荒老人被偷了1.8万元,无奈之下到派出所报案,没想到,这次报案竟意外揭开了老人隐瞒了76年的真实身份。 1938年的河南滑县笼罩在战火硝烟中,十五岁的齐修体放下割草的镰刀,跟着村里十几个青壮年走进了国民革命军195师的征兵处。 这个面黄肌瘦的少年当时还不知道,这个决定将在他的人生里刻下七十六年难以愈合的伤口。 新兵训练场上的泥土被汗水浸透,齐修体每天要背着二十斤重的汉阳造步枪跑上五里地,脚底板磨出的血泡把布鞋染成了暗红色。 老兵教他们装填子弹时总说:"小崽子们记着,枪管子打红了就撒泡尿浇。" 这些粗粝的生存智慧后来在战场上救过他三次命。 台儿庄战役打响那年,齐修体所在连队负责阻击日军增援部队。 他至今记得那个飘着细雨的清晨,阵地上突然炸开的迫击炮弹掀翻了三挺重机枪。 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在晨雾里闪着寒光,齐修体握着发烫的枪托连续撂倒三个敌人,直到左腿中弹跪倒在战壕里。 卫生员用绑腿给他止血时,战壕外传来日语喊杀声越来越近。 被俘后的日子比战场更煎熬,日军在徐州设立的临时战俘营里,齐修体和两百多个战俘挤在牛棚改的牢房里。 每天只有两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,看守的皮鞭抽断了三根。 有个河北籍的排长试图逃跑,被铁丝网缠住脚踝拖回来,活活吊死在营地旗杆上。 齐修体趁着转移战俘的雨夜,藏在运尸体的板车底下逃出生天,在野地里爬了三天才找到部队。 抗战胜利那天,齐修体所在的连队只剩七个活人。 没有授勋仪式,没有退伍证明,团长把最后半袋小米分给众人,说了句"各自回家吧"。 这个参加过五次重大战役的老兵揣着两块银元,拖着残腿走了半个月才回到滑县老家。 县民政局的档案显示,当年像他这样自行返乡的士兵,全县登记在册的就有四百余人。 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,齐修体分到了两亩薄田。 可左腿的枪伤让他干不了重活,庄稼收成总比别家少三成。 1958年公社化运动时,他家被划为"军属困难户",每个月能领八斤救济粮。 可这点粮食要养活五口人,齐修体不得不在农闲时去县城扛麻包。粮管所的工头看他腿脚不便,每天只给算半个工分。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豫北农村时,齐修体已经六十五岁了。 两个儿子分家单过,老两口守着三间土坯房。 村里兴起外出打工潮,可老两口的年纪连建筑工地都不要。 齐修体开始背着蛇皮袋走街串巷,矿泉水瓶、废纸板、烂铁皮,什么能换钱就捡什么。 老伴王秀兰有严重的风湿病,常年卧病在床,药罐子在土灶上熬得咕嘟响。 2014年秋天那个改变命运的早晨,齐修体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出门。 等他晌午回家时,发现藏在炕洞里的铁皮盒不翼而飞——里面装着攒了六年的积蓄,总共一万八千块。 老伴听见动静,从病床上滚下来,抓着空盒子哭得背过气去。 齐修体蹲在门槛上抽完半包散花烟,最后跺了跺脚,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去了派出所。 值班民警看着这个浑身补丁的老人,起初以为就是个普通盗窃案。 可当老人颤抖着说出"我当过国民革命军"时,户籍科的老科长突然想起什么。 档案室里尘封的县志记载,195师曾在当地招兵五百余人,这个番号后来整编入第五战区。 民政局连夜调阅史料,在泛黄的阵亡名录里找到了齐修体的名字——原来部队早以为他战死了。 消息传开后,县城广场的LED屏开始滚动播放老兵的遭遇。 超市老板送来米面油,卫生局长带着专家来给王秀兰会诊,中学生把零花钱塞进红色捐款箱。 最让齐修体感动的是几个退伍老兵组成的志愿者队伍,他们帮着修补了漏雨的屋顶,还申请到了每月八百元的抗战老兵补助金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怀,齐修体总爱坐在村口老槐树下讲古。 他说台儿庄的城墙被炸得跟筛子似的,说战友被燃烧弹烧焦的手还扣在扳机上,说日本兵钢盔下那张长着青春痘的娃娃脸。 有次说到战俘营里饿得啃树皮,旁边听故事的年轻后生突然站起来,把刚买的肉夹馍硬塞进老人手里。 如今在滑县抗战纪念馆里,陈列着齐修体捐赠的退伍证——其实那是志愿者后来帮忙补办的。 玻璃展柜旁的文字说明写着:"这些沉默的老兵,用伤痕见证历史,用皱纹镌刻民族记忆。" 每逢清明,总有人把野花摆放在展柜前,花瓣上的露水在阳光下闪着光,就像当年战壕里未干的血迹。 民政局的档案员去年整理资料时发现,全县登记在册的抗战老兵只剩齐修体一人。 县里特批给他办了职工医保,每个月15号,老人都会坐着志愿者的电动车去银行取钱。 存折上的数字他从不细看,倒是每次都要在营业厅的饮水机前灌满那个军绿色的旧水壶——那是他这辈子唯一的"战利品",从台儿庄战场带回来的日军水壶。 信息来源:抗日战争纪念网——齐修体河南抗战老兵名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