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冬,一名两岁的小女孩在街头奔跑。她的个子不高,穿着略显旧旧的棉袄,脸冻得通红,眼神却亮得惊人。她朝着一个陌生男人跑去,嘴里喊着:“叔叔,快抱抱我!”声音清脆,又急切。 那个男人愣了一下,随后毫不迟疑地弯下腰将她抱起。他的脸被小女孩遮去了一半,手里攥着一张通行证,面对站在一旁的日军宪兵,神色自然。他轻声笑了一下,说这孩子认错人了,是邻家孤儿,总爱撒娇。 日军盯着他良久,却没再深问。小女孩的出现打破了盘查的节奏,也打乱了士兵们的判断。他们最终让那男人离开了。男人抱着孩子走了几步,在转角处停下,低头看着她。女孩仰着脸,嘴角沾着点鼻涕,一脸天真。男人拍了拍她的肩,将她放下,朝另一个方向快步离去。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,也不是最后一次。 几个月后,这个孩子因高烧不退躺在邻居家的床上。屋里没有灯,只有一盏小油灯闪着微弱的光。她的嘴唇干裂,手指冰凉。邻居妇人守着她,来回地用湿毛巾给她擦额头,心里却焦急得很。女孩的父母不在,她的母亲赵梅,正在另一个城市冒充护士,往来医院和宪兵司令部之间,传递情报。她的父亲李振远则已离开了镇子三日,仍未归。 等他们接到消息赶回来时,女孩的呼吸已微弱得几不可闻。李振远一手抱着她,一手撑着她的头,穿过两条巷子、一条小河,去找一个躲藏的老中医。赵梅提着一盏灯,脚步踉跄地跟在后头。可孩子没能撑到天亮。 他们没有哭,也没有叫,只是坐在那间黑屋子里,一动不动。邻居送来一块白布,赵梅接过去,轻轻盖住了孩子的脸。外头风在吹,夜色沉得很。没过多久,他们便离开了这座城。 这对夫妻常年分处两地,几乎不曾团聚。他们的生活,就是化名、伪装、潜伏、传送口令,再化名、再潜伏。他们之间的联系靠旧报纸上的一个点、一张火车票的背面、一句哼唱的小曲。孩子是他们唯一真正的联系,那一份血脉清晰,却在一场病中悄然断开。 在沈阳城郊,赵梅曾扮作一个伪军军官的妹妹,混入高层的晚宴,几番试探后偷出文件。她返回藏身处时,换上旧衣,席地而坐,往嘴里塞了两口冷饭。李振远则曾借口修桥,卧底在一个工程队,手指冻裂仍不敢摘手套,怕被认出身份。夜里他从砖缝中抽出一张纸条,贴身藏好,天一亮又若无其事地背着麻袋进城。 一年里,他们换过七座城市,十八个身份。从伪满洲的宪兵司令部,到日军仓库的搬运工,再到某医院的清洁女工,他们不曾被发现,却也再没机会回头看一次女儿的墓地。墓地在老宅后头,只有一块石片,没刻名字。 有一次,他们分头执行任务,赵梅回得早,在接头点等了整整一天。李振远出现时,脸色苍白,衣角还有血迹。他笑着说:“拖了点时间。”她没问为什么,他也没多说。那天晚上,他们并肩坐在河边,看着远处日军的车队驶过,火光照在水面上,一闪一闪的。 战争快结束时,他们仍在路上。某座小城里,李振远听到广播,说日军无条件投降。他正端着一碗粥,顿了一下,抬头看了赵梅一眼。她没说话,只拿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本子,在最末页写下日期。他们都没有笑。 几个月后,他们在一个政府办公室里登记了真实姓名。办事员问他们有没有子女,赵梅顿了一下,说:“有过。”办事员抬头看了她一眼,没再追问。 多年后,李振远偶然路过那座曾救过他的街口。他站了很久,街边已经是新的商铺,来来往往的行人,没有人认得他。他点了一支烟,吸了一口,烟雾从鼻腔缓缓吐出。他像是看见了什么,又像是什么也没看见。 转过街角,赵梅在前头等着,手里提着一小袋豆腐干。他走上前,两人并肩继续往前走。谁也没说话。风吹着巷口的树,落叶簌簌而下。他们慢慢地走着,像是从一个漫长的故事中走出,又悄悄地,走入另一个无人知晓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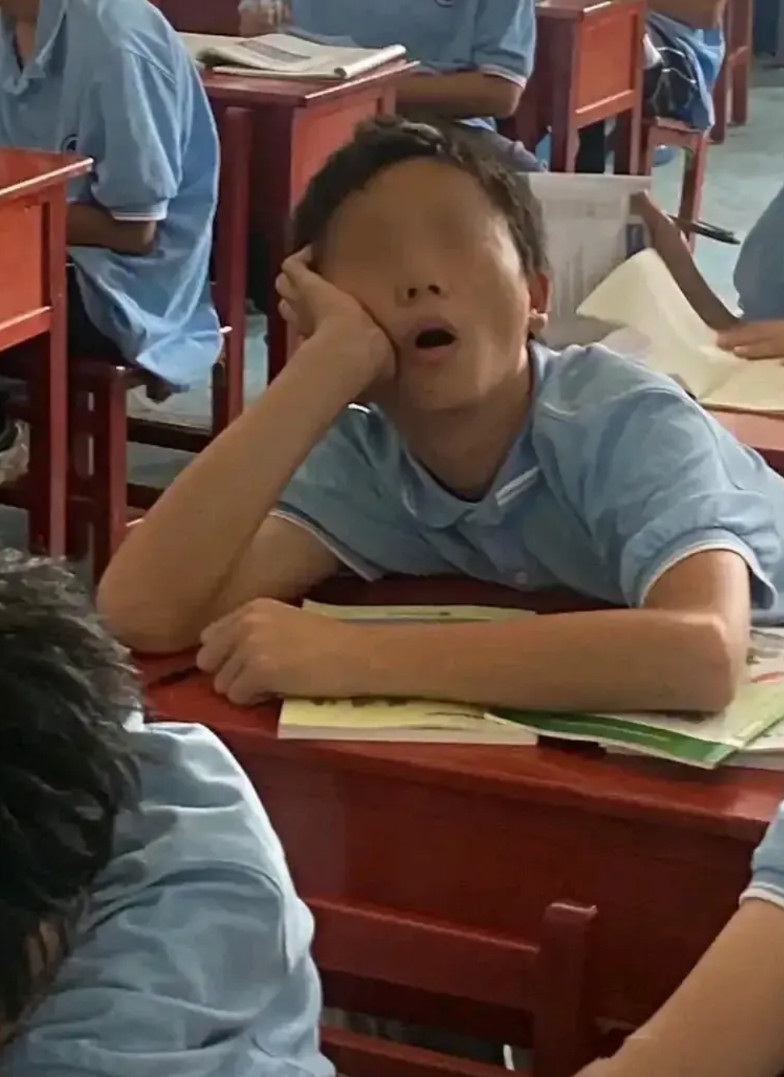



![查分后为了报志愿叫了继父爸爸[鼓掌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1770030175664049281.jpg?id=0)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