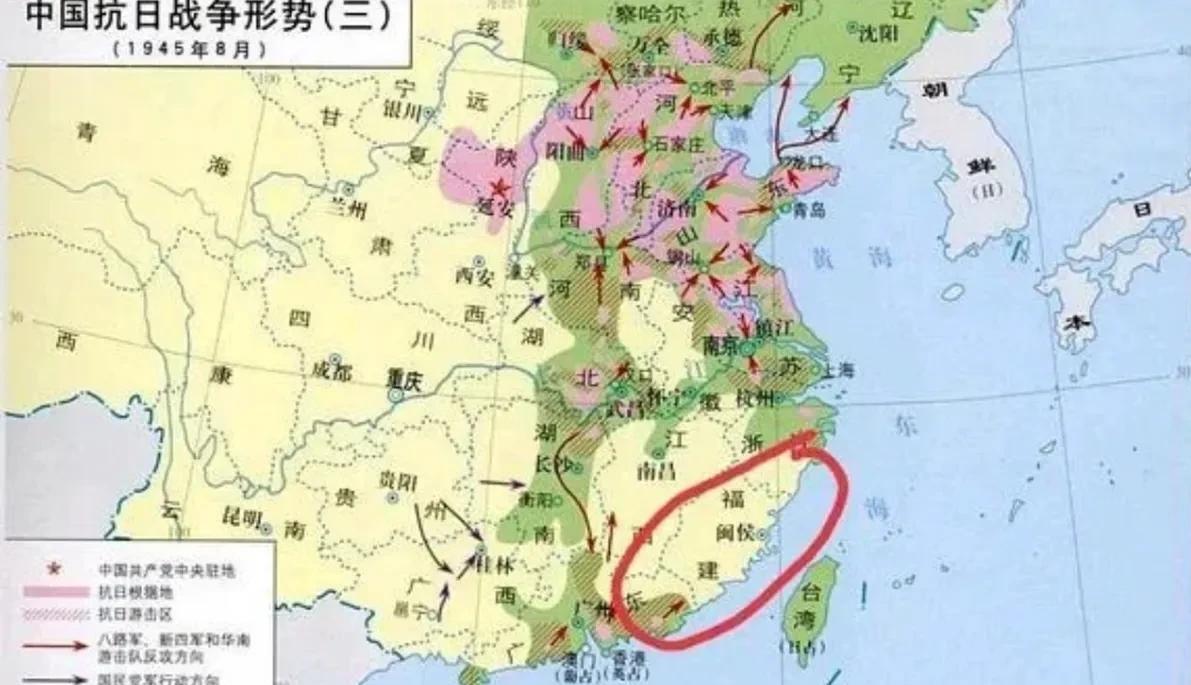1950年9月的一天,一位衣衫褴褛、满脸黝黑的叫花子,来到陕西旬邑马栏镇驻地,邓仕均看到他,立即下跪磕头。
陕西旬邑马栏镇,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田间地头忙着秋收,这天中午,驻地门口来了个拄着木棍的老汉,浑身衣裳补丁摞补丁,脚上的草鞋磨得只剩几根草绳,脸上黑得像是刚从煤堆里爬出来。
站岗的小战士正要上前询问,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只见他们的邓仕均团长像阵风似的冲出来,对着老汉扑通就跪下了。
而这老汉不是别人,正是邓仕均失联十八年的亲爹邓元高。
他们父子二人的重逢,还要从18年前说起,1932年,四川苍溪县山沟沟里,15岁的邓仕均跟着红军队伍走了。
那年月兵荒马乱,家里人只知道儿子跟着红军打天下,可到底是死是活,谁也说不上个准信。
邓老汉和老婆子守着两亩薄田,天天夜里抹眼泪,听见狗叫都以为是儿子回来了。
1950年开春,全国都解放了,邓仕均所在的559团驻扎在陕西搞生产,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18年的他,终于抽空给老家写了封信。
这封信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年,等送到苍溪时,信封都磨出了毛边。
邓老汉攥着信纸的手直哆嗦,识字先生念到"儿现担任解放军团长"时,老汉突然哇地哭出声,把院里下蛋的老母鸡都惊飞了。
没过几天,邓老汉就收拾了个竹背篓,装上二十个玉米馍馍,非要上陕西找儿子。
村里人都劝他:"六百多里山路,您这把年纪哪走得动?"他却说:"当年红军能走,我咋就走不得?"最后是侄子放心不下,背着半袋炒黄豆跟上了。
爷俩天不亮就出发,沿着嘉陵江往北走,遇山翻山,遇河趟水,脚底板的水泡破了又起,草鞋磨烂了七八双。
走到秦岭脚下,带的干粮早就见了底,爷俩白天给人帮工换口饭吃,晚上就睡在村头草垛里。
有回在汉中地界,碰上查路条的民兵,邓老汉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信,逢人就说:"我儿是解放军团长,我要去找儿子!"说来也怪,这话比路条还管用,走到哪都有人给碗热汤面,腾个热炕头。
整整走了十八天,爷俩终于到了西安城,守城的解放军战士看他俩这模样,以为是逃荒的难民,正要往收容所领,邓老汉哆哆嗦嗦掏出信皮上部队番号。
值班排长一个电话打到三原县军部,63军军长傅崇碧听说这事,亲自派了辆吉普车把爷俩送到马栏镇。
要说邓仕均见到亲爹那场面,在场的老兵们记了半辈子,平时带兵打仗雷厉风行的团长,抱着老爹哭得像个孩子。
部队炊事班连夜杀了头猪,司务长翻出压箱底的白面蒸馍,邓老汉却捧着碗小米粥喝得直吧嗒嘴,这一路上饿狠了,突然吃油腥怕闹肚子。
在部队住了小半月,邓老汉可算过上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,儿子给他理了发,儿媳妇扯布做了身新衣裳,三岁的小孙子骑在他脖子上满院子跑。
部队宣传科的人来采访,把老汉的破草鞋和打狗棍收去办展览,说是要教育新兵什么叫"革命家属的坚韧精神"。
但好日子没过多久,部队就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开,。邓仕均带着队伍往东北赶的时候,邓老汉正在回四川的火车上啃儿子塞给他的压缩饼干,谁也没想到,这次分别竟是永别。
1951年5月,邓仕均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中壮烈牺牲,时年34岁,消息传回国内时,邓老汉正坐在村头大槐树下,跟乡亲们讲儿子部队里的新鲜事。
后来县里民政局的干部上门送烈士证,邓老汉没哭没闹,就问了句:"我儿走的时候,可还体面?"听说是带着队伍冲锋时中的弹,老汉点点头,把烈士证供在了堂屋祖宗牌位旁边。
信息来源: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《抗美援朝战争史》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《苍溪县志》、原63军老兵回忆录《铁血雄师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