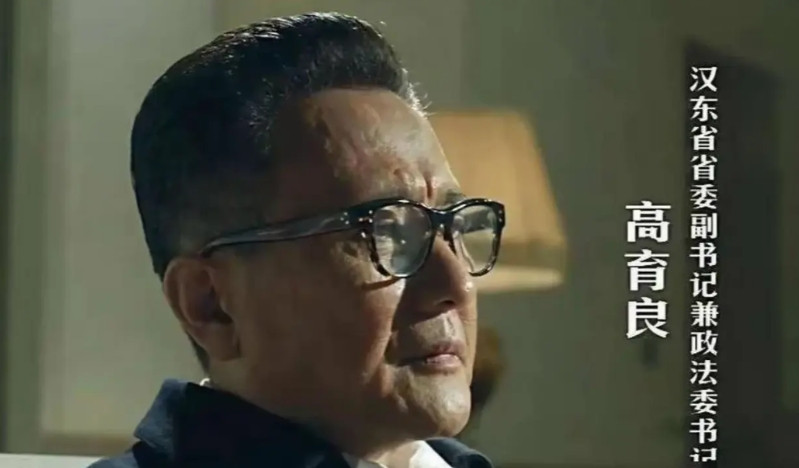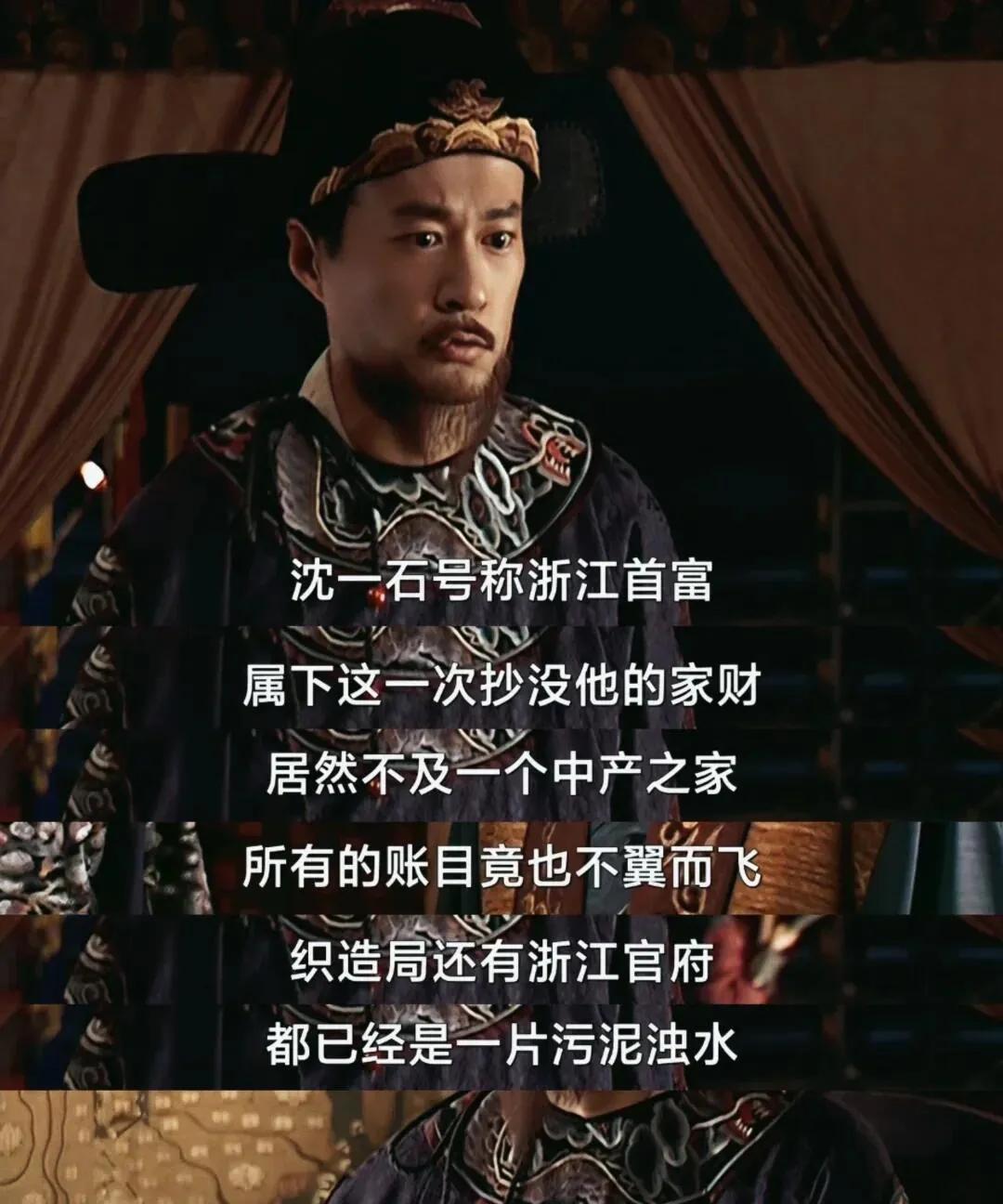1959年,陈长捷出狱后,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,陈长捷故意姗姗来迟,看到傅作义的那一刻,他马上厉声告知,按照过去自己的脾气,绝不会前来就餐!
1959年北京西单饭庄里,两个年过花甲的老军人上演了一出特殊的重逢戏码。
陈长捷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,故意踩着钟点迟到三分钟。
当他在包厢门口瞧见傅作义那张圆润发福的脸,喉咙里像卡了块烧红的炭,要不是服务员端着热汤从身后经过,他真能当场摔门走人。
1907年福州郊外,陈家第七个男娃刚落地,他娘瞅着空荡荡的米缸直叹气。
陈长捷打小就懂得看人脸色,五岁跟着哥哥上山砍柴,七岁蹲在祠堂门口帮人抄写族谱。
要不是遇上开明先生田春干,这小子八成要在乡野间埋没一辈子。
田先生不仅供他念书识字,还把自己闺女许配给他,这份恩情陈长捷记了半辈子。
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报到那天,傅作义拎着藤条箱子差点撞翻陈长捷的砚台。
两人同住八人通铺,山西口音混着福建腔调,竟也结下过命交情。
傅作义脑子活泛,陈长捷踏实肯干,毕业后双双投奔阎锡山麾下。
要说陈长捷打仗是真有两把刷子,忻口会战带着72师硬扛日军精锐,七天七夜没合眼,愣是把鬼子逼退三十里,报纸上都叫他"陈铁头"。
1948年深秋,天津城防司令部电话铃响得能震碎玻璃。
陈长捷攥着听筒,耳朵里灌满傅作义"死守待援"的命令。
他哪知道老同学正在北平跟共产党代表谈判,还当是效忠党国的最后关头。
解放军的大炮把城墙轰得直掉渣,守军伤亡名单摞起来有半人高,陈长捷还咬着牙给部下打气:"傅长官说援军在路上!"
等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,陈长捷正在战俘营啃窝头。
功德林的铁门咣当关上那刻,他恨不能生撕了傅作义。
后来听说傅作义当上水利部长,他蹲在牢里把搪瓷碗都摔变了形。
狱警送来报纸,头版登着傅作义视察官厅水库的照片,他抓起报纸就要撕,忽然瞥见照片角落里站着当年太原会战的老部下,手一哆嗦又把报纸捋平了。
傅作义头回来探监是1953年开春,隔着铁栅栏,陈长捷梗着脖子不拿正眼瞧他。
管教干部说傅部长每个月都往这儿寄书,从《论持久战》到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每本都用牛皮纸包得齐整。
陈长捷把这些书全垫了床脚,直到有天夜里老鼠啃书皮,他随手抄起本《孙子兵法》,借着月光看到东方既白。
1959年特赦令下来那天,陈长捷在释放名单上找了三遍自己的名字。
管教干部塞给他个蓝布包袱,里头有套新做的中山装,夹层里塞着傅作义亲笔信。
信纸上的墨迹被雨水洇开过,最后那句"当年事,是我对不住兄弟"皱皱巴巴的,倒像是写信的人掉了眼泪。
西单饭庄那顿接风宴,八仙桌围坐着十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
陈长捷进门时故意碰翻了门边的青花瓷瓶,碎瓷片溅到傅作义皮鞋上。
满屋子人倒抽冷气,傅作义却笑呵呵地蹲下身,掏出白手帕把碎瓷片一片片捡起来。
服务员要过来打扫,他摆摆手说:"岁岁平安,好兆头。"
酒过三巡,陈长捷突然把筷子拍在桌上。
满桌佳肴跟着震了震,水晶虾仁从转盘滑到桌布上。
傅作义不紧不慢夹起虾仁放进自己碗里:"天津卫的虾仁比这个脆生,等开春咱们回去尝尝。"
这话像根针,把陈长捷憋了十年的怨气全扎漏了。
他想起当年傅作义来天津视察,两人在起士林吃俄式大菜,窗外海河结着薄冰。
散席时飘起小雪,傅作义把自己的呢子大衣往陈长捷身上披。
两人沿着长安街往南走,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。
走到电报大楼门口,傅作义忽然说:"上个月我去天津,老城墙根儿那棵槐树还在。"
陈长捷鼻子一酸,当年他们就在那棵树下合计怎么布防。如今树还在,城早不是那个城了。
开春后陈长捷真去了天津,傅作义派秘书全程陪着。
站在金刚桥上望海河,当年架着机枪的桥头堡变成了卖煎饼果子的小摊。
摊主是个瘸腿老汉,听说陈长捷是当年守城的,多给他加了俩鸡蛋。
陈长捷捧着煎饼蹲在桥墩子底下吃,烫得直咧嘴,眼泪却吧嗒吧嗒往油纸上掉。
后来陈长捷在上海文史馆做事,傅作义每次南下都要找他吃茶。
1966年傅作义最后一次来,两人在城隍庙吃了碗酒酿圆子。
傅作义把圆子汤喝得干干净净,临走时说了句:"当年要是早点喝上这口热乎的..."话没说完,摆摆手钻进吉普车。三年后傅作义病逝,陈长捷对着北方鞠了三个躬,腰弯得比谁都低。




![这武力值爆表啊,放在古代就是一猛将兄[666]印巴之间在打高科技现代化空战,中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577367793292164561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