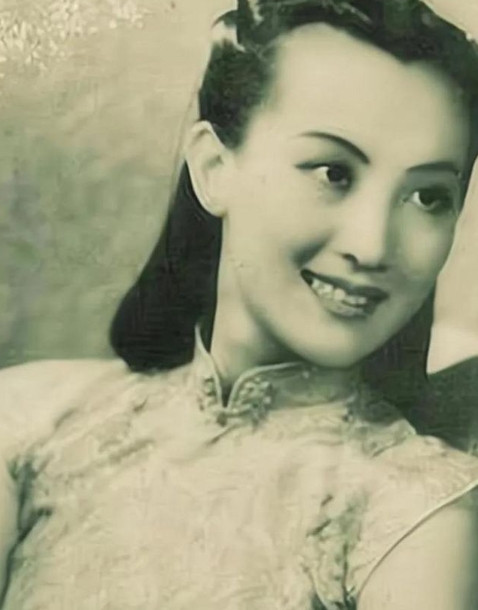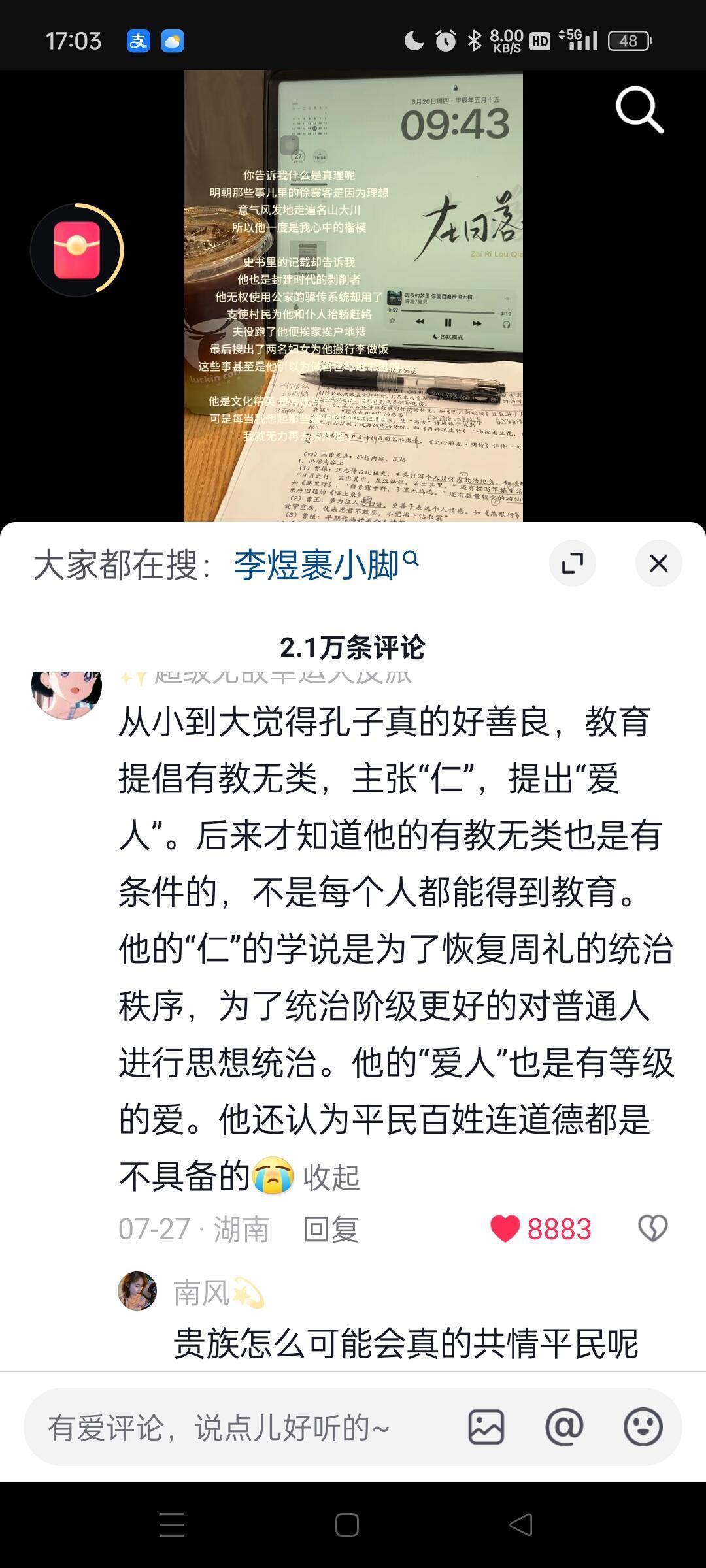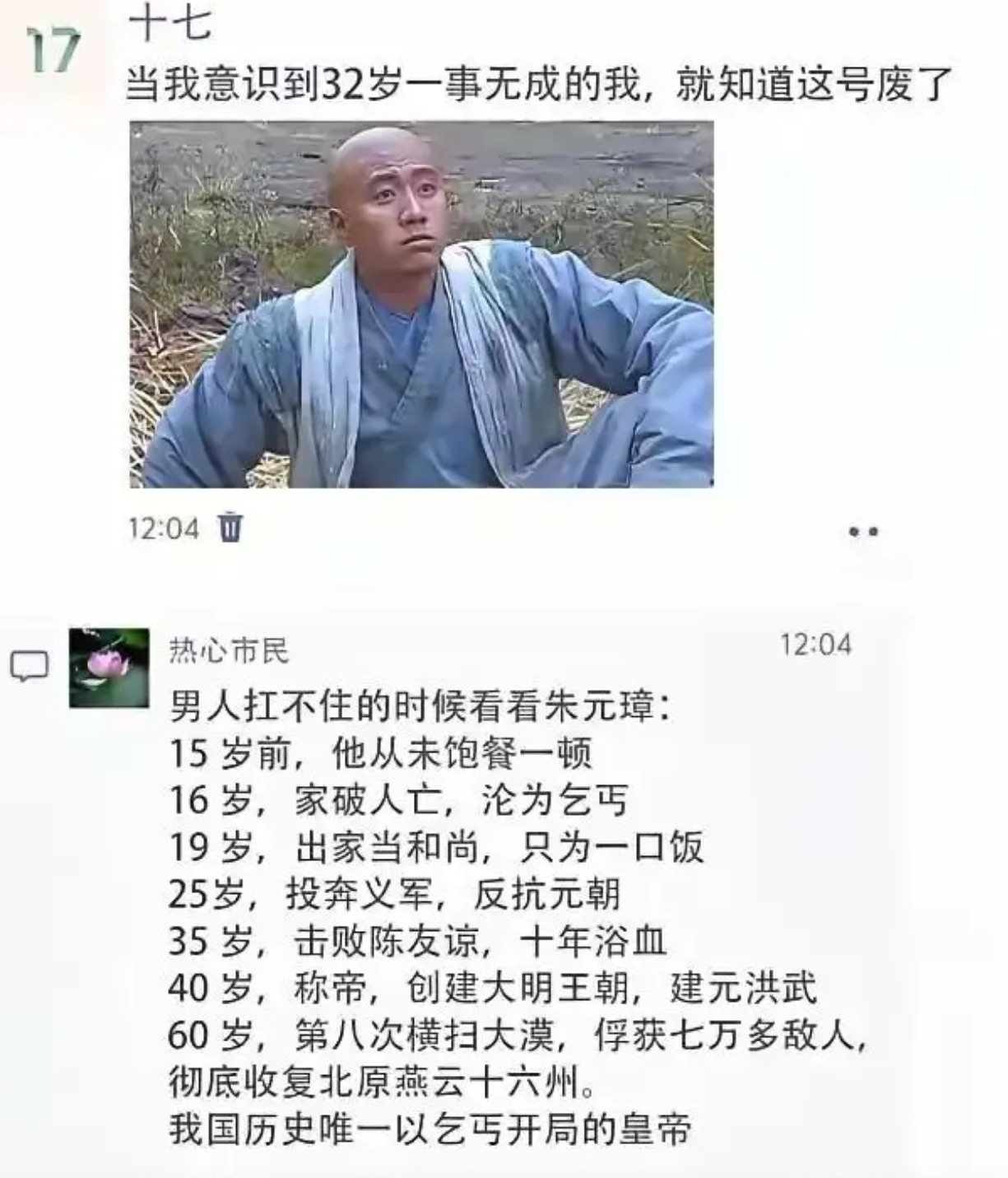1939年冬,董士沅在账本边上写下一句:“油一两四角八,米一斤五角二。”他是合肥一个货栈掌柜,眼睁睁看着手里的银元变成废纸,房租收不上来,饭桌上没了鱼肉,只剩干馒头。 他曾经穿长衫、读报纸、讲规矩,算是本地有头有脸的生意人,可战争一来,他成了没活干、卖字画、吃开水馒头的“穷讲究”。 1936年,董士沅的日子还过得体面,他管着一家商号,月薪连同利息、分红加起来有一百多块银元。 他会花五毛钱去澡堂蒸个桑拿,顺手赏给伙计二毛的“小费”,闲时还会请人吃茶讲《孟子》。 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,每天的支出都算得仔细,哪怕是“理发四分”“酒钱一角”,也没落下。 他不是大富,但稳定,那时的中产阶级讲求的是面子、规矩和稳定,他买书不手软,常买《法律质疑汇刊》《铁道史》,连《史记》都翻过。 家中有藏画,墙上挂着字帖,还雇了个临时小工帮忙搬东西,他不是那种天天应酬的暴发户,但在那个年代,也算日子过得“讲头十足”。 1937年卢沟桥一响,局势全变,第二年,日军攻进安徽,董士沅的商号关门,他不再是账房管事,而是无业游民。 他搬出自家大宅,租人家屋檐底下的旧屋子住,账本上开始出现“房租收入10元”,说明他靠租房维持生活。 这还不是最惨的,后来连这十元都常常收不上来,房客自己都吃不饱饭了,哪有钱交租? 没有固定收入,吃喝用度一天天缩水,1938年起,账本上有关“点心”“糖果”的项目几乎消失。 他以前爱吃的糕点,什么蜜三刀、麻花,统统没影了,只剩“购馒头三枚,三分”“茶水一壶,二分”这样的记录。 他吃饭不是讲究,而是将就,为了省钱,他把洗澡和理发也分成两次进行,以前是一并办妥,现在是理一次发,等半个月再洗一次澡。连张脸都要省着花钱。 原本一个文化人,慢慢走上变卖家底的路,他开始卖字画,一张张曾经挂在墙上的墨宝拿去当旧货换饭吃。 还有几次,账本上写了“算命一元”,他开始去问命问运,想看看这倒霉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。 有一年,他还花了两角请人写对联,贴在门上也不是为了喜庆,而是求个平安。 账本的笔迹也变了,原来写得端正、整齐,有板有眼,到了1940年后边缘处总有涂涂改改,甚至写些私话,比如“心不安,米价又涨。”这些不是记账,是心声,是他那点挣扎着想过下去的劲头。 最难的是1941年。那一年,米价飙到战前的40倍,他的账本记录:米一斤五角二,而他的月收入还不到十五块,光是买粮食就吃掉了三分之二的钱。 那时候,他每天去同一个米铺,问价格,从来不敢马上买,他怕买了以后明天又跌价,但往往是再等一天,就涨了。 以前他每月还能省点钱买本书,那年只买了一本《心经》。他在账本上写了“心经一册,一元”,这是他最后的精神支柱。 过去是读史书、法律,如今改读经文,连信仰也在转,他想靠经书稳住自己的心,可心还是乱的,他在账本空白处写下:“旅人心绪,不言而知。” 他不是没想过出路,有一次他花一块五买了一本《英汉辞典》,还标注“为日后学用”。可现实太骨感,他连饭都快吃不上了,还学什么外语?但这也许就是最后一点希望,哪怕这希望是奢侈的。 董士沅的日子并非孤例,那个年代的中产,多数都像他一样夹在中间,上不着天,下不挨地。 富人可以转移资产,有的人把黄金藏在米缸里,有的干脆送子女去香港、南洋。 甚至有人靠捐钱给伪政府“换平安”,比如某富商一次性捐三千买了“良民证”和“特供配额”,照样吃肉喝茶。 底层的老百姓虽然穷,但不少人有自留地,粮食还能种些出来,自给自足不容易饿死。 而董士沅这类人,靠工资、靠利息,一旦断了就啥也没有,连去当苦力的门路也找不着,人到中年,文不能武,去码头抬包没人要他。 账本上记的,不只是数字,是一段阶层崩塌的缩影,他用一笔一画写下一个中产阶级从“有规矩的体面人”变成“靠卖画混日子”的过程。 文化、收入、面子,一样样被打散,他不偷不抢,不怨天尤人,就每天坐在油灯下翻那本账,看今天是不是还能勉强过得去。 战火烧的不只是城墙,也烧掉了一个社会结构,董士沅的故事,让人看到战争最无情的地方,不是让你死,而是让你活得不像个样子。 他还活着,却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,原来稳稳当当地立在城市的一角,现在风一吹就摇得厉害。 张鸣. 晚清与民国的中产阶级. 北京: 三联书店, 2015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