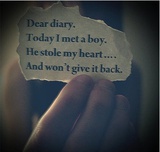“不知廉耻。”1927 年,一个名叫卫清芬的女子不穿束胸,被公婆咒骂。警察知道后,却让公婆交了50块大洋,这是为何? 1927年的广州街头。卫清芬趁着公婆不注意,偷偷扯下裹在胸前的白布条。 她深吸一口气,感觉胸膛里像卸下块大石头。 可这口气还没喘匀,婆婆的骂声就追到耳朵根:“不要脸的赔钱货!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!”老头子抄起笤帚就要打,吓得卫清芬赶紧把布条又缠回去。 这白布条可不是普通物件。打从卫清芬十三岁起,她娘就拿着两丈长的白布,像捆粽子似的勒住闺女日渐鼓胀的胸脯。 出嫁那天,婆婆盯着新媳妇平坦的前襟直点头,转头就把束胸的差事交给了儿子。 如今二十出头的卫清芬,胸口早勒出两道紫红的淤痕,喘气都带着嘶嘶声。 要说这束胸的讲究,得从宋朝说起。那时候读书人讲究“存天理灭人欲”,把女人胸脯鼓起来当成勾引汉子的罪过。 到了明清两代更邪乎,官家小姐要是敢挺着胸脯出门,能被唾沫星子淹死。 民国都十六年了,城里女学生反倒学起老古板,个个穿着紧梆梆的小马甲,把胸脯压得比男学生还平。 可世道到底在变。1915年上海《妇女杂志》登了篇文章,说束胸比裹脚还害人。 这话像颗火星子,溅到新派知识分子的心坎上。留过洋的胡适先生在女校演讲时拍桌子:“没奶水的娘能养出壮实娃? 咱们这是在断子绝孙!”这话虽糙,理却不糙。广州城里的报纸跟着起哄,天天登些束胸女子得肺痨的病例。 转年开春,广东省政府出了个新鲜章程。民政厅长朱家骅领头写的文书,白纸黑字写着:三个月内全省妇女必须放胸,违者罚五十大洋。 这数目可不小,够普通人家吃半年白米饭。卫清芬头回听说这消息时正在井边打水,手一抖差点把水桶掉井里。 要说这朱厅长还真是个狠角色。他让人在城门口贴告示,派女警察上街巡查。 那些缠着小脚的阿婆们凑在告示前嘀咕:“作孽哟!大姑娘挺着胸脯满街跑,成什么体统?”可牢骚归牢骚,真见着戴大盖帽的女警察过来,老太太们跑得比谁都快。 卫清芬头天解了束胸带,刚出门就撞见邻居王婶。 这老婆子眼睛毒得很,隔着粗布衫都能瞧出端倪。当天晌午,两个女警察哐哐砸门,罚单开得利索。 公公梗着脖子嚷嚷:“老子有的是钱!”可没过半个月,警察又来敲门。这回老头子手抖得连钱袋都解不开——家里攒的棺材本都快见底了。 城里像卫家这样的倔骨头不在少数。有户卖豆腐的人家,闺女放胸后愣是被锁在阁楼里。 最后还是街坊举报,警察扛着梯子翻墙进去救人。这事儿传开后,茶楼里的说书先生都拿来当段子讲:“如今这世道,当爹娘的管天管地,管不着闺女胸口二两肉!” 要说变化最大的还得数年轻姑娘。原先裹得粽子似的女学生,现在敢穿洋布衫上学了。 有个叫孙舞阳的进步女性,在报纸上写文章说:“咱们的胸脯不是腌菜坛子,非要压扁了才好看。” 这话传到乡下,把卫清芬的婆婆气得直拍大腿:“伤风败俗!伤风败俗!” 转眼到了1930年,广州城里的风气彻底变了样。百货公司橱窗摆着西洋来的胸罩,电影明星阮玲玉穿着高开叉旗袍登报。 卫清芬现在赶集时敢抬头挺胸走路,虽说遇见老街坊还会脸红,但心里头舒坦得像三伏天喝了井水。 有回她碰见当年开罚单的女警察,人家反倒夸她:“早该这样,多精神!” 那些死抱着老规矩的人,就像秋后的蚂蚱——蹦跶不了几天。 如今的姑娘们讲究自然健康,倒是那些束胸的老物件,都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。 前些日子报纸上说,有个老太太把祖传的束胸带捐给妇女儿童博物馆,说是要让后辈知道,他们的奶奶辈曾经遭过这样的罪。 信息来源: 百度百科:束胸 妇女研究论丛:《解放乳房的艰难:民国时期“天乳运动”探析》 民国日报:天乳运动专题报道 广东省政府档案:《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》 妇女儿童博物馆:束胸带文物说明 北洋画报:天乳运动社会观察专栏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:民国服饰改良记录 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:朱家骅社会改革文集